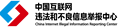口弦 | 我的醪糟情結
記憶只有不斷地重溫才能長久地珍藏,兒時的美好記憶之所以甘若醴酪,是因為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地強化記憶和演繹,使醇香與完美并重。
20世紀80年代初,和當時大多數家庭一樣,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也很困難,飲食單一。記得那年秋天,我和母親去固原城,進城是許多鄉(xiāng)下人,尤其對于鄉(xiāng)下孩子來說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。
固原有個南門坡子,與南河灘相接,當時是固原最繁華、最熱鬧的商業(yè)街。母親領著我在人群中擠來擠去,我對周圍的一切充滿了好奇,東瞧西看,目不暇接。
南門坡子確實有坡,一條南北走向的緩坡,柏油路面,不算寬且年久失修,有些斑駁、有些不平,但這并不影響這里的熱鬧。除了熙熙攘攘的人群,還有自行車、架子車、驢車等時有往來,空氣中似有塵土和牲口的尿騷屎臭味,街道兩側鱗次櫛比地擺滿了地攤。
我被母親拽著,不知去哪兒,也不知要買什么,更辨不清東西南北。當我們來到半坡位置時,有絲絲甜甜的香味撲入了我的鼻腔,我循著香氣在地攤中尋找,發(fā)現是來自街道左側的一處小吃攤。不知是餓了還是渴了,我站在那里再也不走了,母親拽不動我,便停下腳步,猶豫再三決定滿足一下我的欲望。
那是一個沒有任何廣告標志的小吃攤,最顯眼的是一個比水桶還細的小鐵皮爐,爐子上擱著一口被熏得黝黑的小鍋,蓋著木質的鍋蓋,鍋下火苗舔著鍋底,香氣伴著熱氣從鍋蓋縫里擠出,甜甜地勾著路人的食欲。爐子下方一條管子用來鼓風,管子的另一頭有一個小木箱,這個我認識,叫風匣,我們家里就有,不同的是我們家的推拉桿是兩根,而這個只有一根,細細的。隨著風匣桿的推拉,爐火時緊時慢,伴著青煙和火苗。坐在爐子后面的是攤主,一位年長的老奶奶,她神情專注,既不攬客也不吆喝,旁邊擺著一張極小的方桌,四方小板凳,一方板凳上有人,應該是等待的顧客。
我怯怯地隨母親坐下。
“來兩碗。”母親輕聲說。
“嗯。”老人點著頭應了一聲。
經過漫長的等待,終于輪到給我們做了,我睜大眼睛,伸長脖子仔細看。老人動作嫻熟,她先從水桶里舀出一瓢水倒入鍋中,不緊不慢地推拉著風匣,等水燒開,她揭開旁邊一個陶瓷罐的蓋,從中舀出兩勺米少水多的湯汁添入鍋中,后來我才知道,那湯汁就是醪糟。隨著風匣的繼續(xù)推拉,火苗漸漸小了,老人移開鐵鍋,加入了一小鏟炭塊,頓時火苗、青煙同時騰起,與鍋蓋縫隙中溢出的熱氣彌散開來。我聞到一股淡淡的甜香,口中生津,咽了一口唾沫,眼睛直勾勾地盯著鐵鍋。
在燒火的間隙,老人快速地在碗中打了一個雞蛋,用筷子攪拌均勻。等老人再次掀開鍋蓋時,已開了鍋,屈指可數的米粒隨著水浪游走,老人停止燒火,小心翼翼地將一半蛋液旋轉著瀝入鍋中。等我回過神的時候,兩小碗雞蛋醪糟湯已擺到了我和母親面前,母親幫我攪了攪,說涼點更好喝。一勺入口,滿口香甜,甜味在唇齒之間回旋,味蕾的刺激讓我加快了速度,一勺接著一勺,最后端起碗一飲而盡,舔舔嘴唇,回味無窮。
這是我人生喝的第一碗醪糟,從此便深深地刻入了記憶,它的味道似乎融入了我的靈魂,終生難忘。
此后一年多,我再也沒有喝到醪糟,但那種香甜的記憶和食欲一樣越來越濃烈,每次母親去固原,我總纏著她帶上我。
當我第二次隨母親進城,南門坡子已發(fā)生了不小的變化,地攤減少,門店增多,街道寬敞干凈了許多。當我舊味重尋時,發(fā)現醪糟攤位多了三四家。幸好之前的那位攤主老奶奶還在,風匣換成了手搖鼓風機,桌凳升級換代,醪糟湯米粒似乎多了一倍,雞蛋變成了兩碗用一個,甜香味更醇厚,一碗下肚,甜美直入心間,暖暖的。這次舊味重溫,使我的醪糟情緣更加深厚。
此后一年,我們家遷入固原,雖然去喝醪糟方便多了,卻因各種原因沒再去南門坡子醪糟攤點。
進入上世紀90年代,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進步,地攤變得越來越少,專賣醪糟的地攤也隨之絕跡,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、物質條件的改善,各家都具備了做醪糟的條件。
母親的廚藝很好,我堅信通過母親的雙手,我一定能找回曾經的醪糟味,遺憾的是母親早逝,給我的醪糟情結打了一個大大的結。
后來,喝到醪糟已不再是什么難事,但我總挑剔味道的瑕疵:或太甜、或太寡淡、或有酸味……無法達到我記憶深處恰到好處的甜淡。
要想可口,自己動手。于是我自己動手嘗試做醪糟,這件看似簡單的事做起來并不簡單,雖然會遇到選擇米的種類、蒸米的硬度、甜酒曲的量、配水量、水溫度、封存溫度和時間等一系列的問題,但我依然樂此不疲,只為尋找記憶中的味道,只為那不了的醪糟情結。
現在,我還是隔三差五地喝醪糟湯,但懶惰作祟,只能買超市里的醪糟罐頭來告慰我的醪糟情結。
記憶有時候會強化成為一種習慣,這種習慣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日常生活。人們點菜好像有個約定俗成,最后環(huán)節(jié)至少要點一個湯。有時被人請去點菜,不管婚喪嫁娶,還是慶祝聚會,醪糟成了我的首選。有時我也為此苦惱,似乎由于我的偏愛綁架了別人的味蕾,有時為了刻意改變,少不了在醪糟上糾結許久。(通訊員:馮順恒)